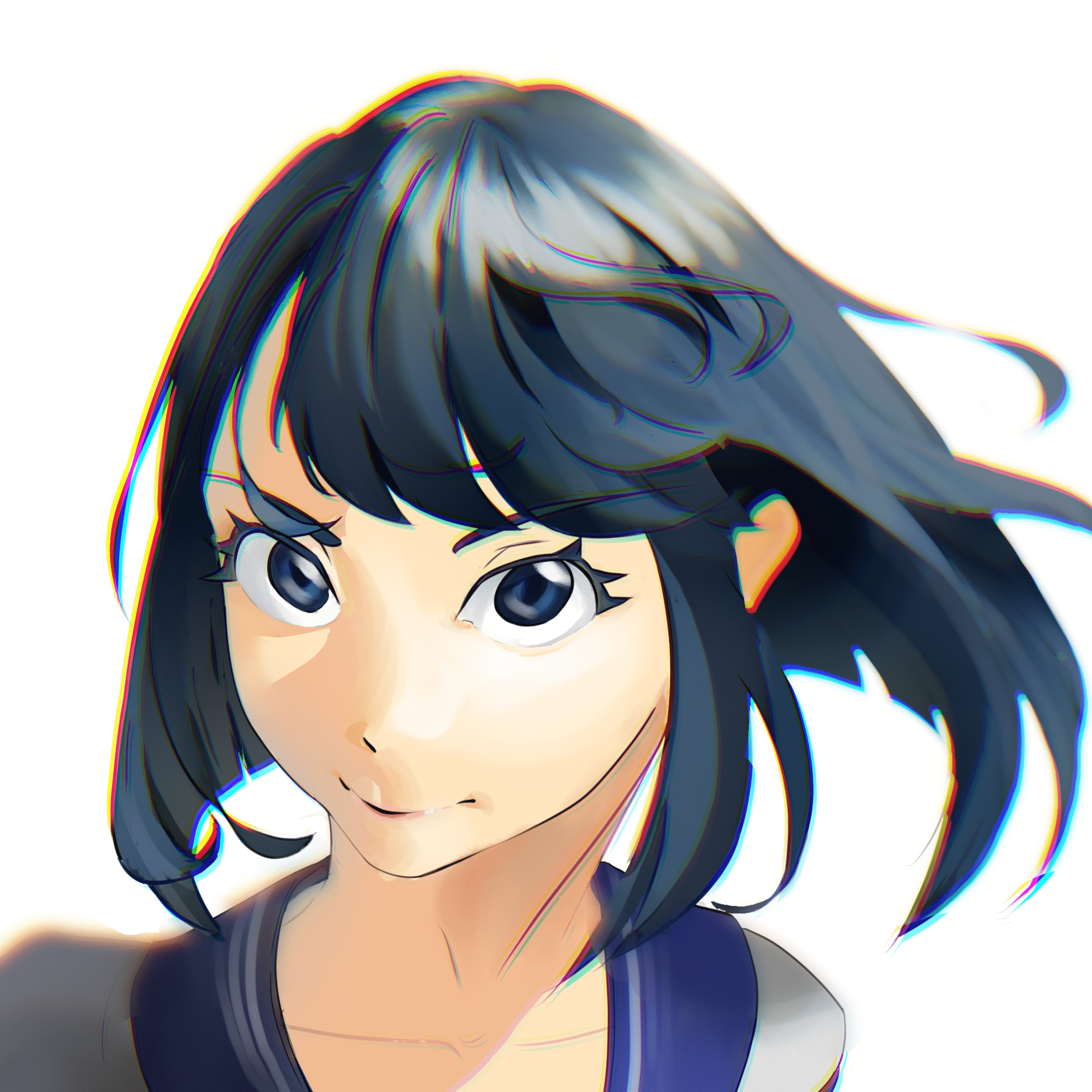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權利,就是「讓別人失望」的權利。
國中的時候因為真的很喜歡畫畫,甚至大家都還在猶豫第一志願該填什麼的時候,我早已經表態要讀設計科。
但是生涯規劃老是播「設計科出路最慘」的影片,害每次同學都一定先關注我這個「未來的輸家」還要不要讀設計科。
每次的關注讓我動搖信念,愈發相信設計科的選擇不正確、不體面。
為了不要當輸家,我選了任何一個人都沒料到的高職,而且還是數一數二低分的森林科。
雖然森林科不如普通高中「正常」,但比起薪資最低的設計科,至少能夠因為「特殊」而贏。
然而,正如喬瑟夫‧坎伯在《千面英雄》所說:
把耳朵轉向聽聞其他有趣的事,他的繁榮世界變成枯石荒原,生活沒有意義。
高分低填帶來學業平步青雲的優勢,只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寧靜而已。
自從拒絕生命的召喚之後,無論「蓋的是什麼房子,都將是死亡之屋。
因此只能替自己製造新的問題,並等待逐漸逼迫的解體。」
森林科經歷過多次人際關係挫折之後,我整個人近乎瘋狂。
原本隨和的個性變得緊迫逼人、憤世嫉俗跟悶悶不樂,恨不得離開這個挫敗我的世界。
也許是憤怒的力量,讓我真的離開農科,奇蹟般考上農科生近乎考不上電影系,如願脫身於那個挫敗我的世界。
然而,轉往電影系之後,也沒有好到哪裡去。
壓抑的繪畫慾望還是沒解決,人際關係的挫折,果真如神話般輪迴。
猜測他人心意,迎合環境期望等等精神折磨,消耗掉大量腦力,根本無暇顧及自己是誰,該做什麼,又該往哪去……
結果就是,讀了四年的專業能力也沒有半點長進,不如自己想像中的完美,不如當初預期的那樣順遂。
幸好「命裡有時終須有,命裡無時莫強求。」
這些年來,繪畫卻從未拋棄我。
它老是在我命運最低迷的時候出現,邀請我隨時可以回頭。
如同聖經裡的耶穌三次呼喚彼得,繪畫也召喚我三次,但三次我都沒有回應。
第一次是森林科一年級的樹木識別要畫標本,三年只有那堂課可以畫畫,每次都期待上完課畫作業。
只不過一年級之後就再也沒有要畫畫的課,但我也沒有追隨繪畫。
第二次是升上電影系的大一突然想要畫素描,開始考慮要怎麼同時在電影系,又同時能夠畫畫。
幾經研究之後,發現電影美術可以畫圖,又能拍電影,豈不美哉!
只不過電影系的美術組都在生道具跟搬道具,根本沒有美術設計,倒是滿常設計死自己。
最後一次是我本來一直「以為」自己喜歡古典好萊塢跟日本老片,一直覺得要看那些經典電影才會受人喜歡,所以一直假裝「品味高尚」。
直到大三開始深陷宮崎駿、押井守跟大友克洋等等動畫電影,甚至大三、大四寫的短篇和長篇劇本也是動畫向,而非寫實向,我才知道原來之前那麼累,全都是因為我在「迎合」電影系的期待。
但其實跟岸見一郎說得一樣:「也許根本就沒有人那樣期待過。」
拒絕自性的呼喚(Self),生命就會以痛苦和挫折暗示你回頭。
這三次的拒絕召喚,讓我嘗盡苦頭。人生耗費整整7年在不屬於我的海域裡漂泊。
完成畢業製作之後,也許是再也不需要活在「名為電影系學生」的期待之下,也可能單純是吃飽沒事幹,終於動筆畫圖。沒想到一畫就帶來了三樣重大改變!
最明顯的改變是好奇心。一開始只是買了網路推薦的施德樓鉛筆,沒想到畫具的探索不減反增,品牌除了最一開始的施德樓,現在還有輝柏、COPIC、Koh-I-Noor、Uni跟卡達,種類也從素描鉛筆,擴增到麥克筆、油性水性色鉛筆、油性粉彩、粉彩、代針筆和工程筆。不太愛出門的我,也難得出席上週五的動畫講座,實屬不易哈哈。
再來改變是完美主義。本來不管怎麼改都改不掉的拖延,以及根植於自卑而衍生的完美主義,在電影系的專業發展上拖了很大的後腿,然而,繪畫卻讓我不藥而癒。我再也不會依靠作品證明自己,我只「想要畫」。
最後一個仍在努力的改變是人際關係。道理很簡單,一旦學會向內關注,一旦能自己關注自己,就不再需要渴求別人的關注。這點才剛體悟到,還不甚穩定,唯一能知道的是狀況比前二十年好太多了。
「我發現我的所有思緒都像行星圍繞著太陽一樣,圍繞著不可抗拒的上帝運轉。」
榮格所說的上帝,不是某位白鬍子老頭,而是居住在我們內心深處,那位真實健全的自我。
當我們的內心有真理,任何虛假期待,都無法蒙騙跟取代內心的光芒。
諾貝爾獎得主理查‧費曼曾經說過:
你管別人怎麼想?(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?)
我們太常把別人的劇本拿來演自己的人生,卻忘了觀眾席除了自己以外,其實空無一人。
即使真的有誰拿自己的期待要求我們,我們也「沒有義務做到別人認為應該完成的事情,我也沒有義務要成為他人預期的模樣。」
真理總是來得太晚,同時也來得剛好。
要不是有像是《奧德賽》的輾轉經歷,要是當初直接投身設計科,我現在可能只會覺得自己像條狗在設計自己,不會意識到繪畫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。
現在我知道,自己不需要成功,也不需要聽話,只需要是自己。
我拒絕了父親對我安穩生活的期望,
拒絕了生涯規劃告誡設計科薪資最低的期望,
拒絕了森林科學生就該直升森林系的期望,
拒絕了電影系學生就該拍電影的期望,
拒絕了一切非我之後,終於承認我要畫圖的渴望。
現在,雖然不知道前方具體道路是什麼,也深信一定會遇到許多阻礙,但我相信我走在通往社會不正確但生命正確的道路上。
如果你下個月會死,你這個月願意拋棄什麼,去換得什麼?